《我左乳的最后日子

你真该看看我的奶子.现在。它们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右乳是a罩杯,是一个小而柔软的肉丘,上面有一个半美元大小的粉红乳头。它很熟悉,看起来很像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过的无数照片和电影里的样子。虽然不会妨碍交通,但看起来不错。另一方面,我的左胸,也许能阻止交通。这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哈密瓜大小,皮肤绷得紧紧的,侧面还有长长的黑色缝线。乳头是粉红色和深紫色的迷幻漩涡。它的中心是黑色的。黑色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佩服这种进步。伤口已经愈合了,除了乳头,皮肤的颜色也逐渐恢复正常。一周前,我的胸部出现了巨大的黄、绿、紫相间的淤青,周围有一圈皮下塑料管连接着一个排水灯泡。
一周前,它看起来和它的邻居很像。我的胸部参加了乐队训练,为可可眼镜蛇和杀手乐队的重聚表演做准备,在卡斯卡德运动俱乐部游泳,还在三份工作中拼命工作:脱衣舞、调酒师和写作。12年后,它也在玛丽俱乐部(Mary’s Club)的舞台上最后一次亮相——在它的绝唱——滚石乐队的《Doncha Bother Me》(Doncha Bother Me)的整个旋律中,它赤裸而骄傲,以数千次呼吸起伏,坚忍地掩饰着一颗疼痛、悲伤的心。然后,在2008年9月26日,它屈服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除了一些已经扎根的微小癌症碎片。
以下是我在乳腺癌的荒野中旅行的见闻,也是对一个身体部位的颂歌,它总是超过它的工作。
谢谢你的回忆。
《安息吧

新家:医生的办公室
图片:拉斯维加斯万岁
肿块
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我entrée进入乳腺癌的世界始于一个肿块,是我以前的情郎在一次例行的“乳房检查”中发现的。这个肿块并不难发现:我的乳房不过是肿块,而且肿块上的肿块,嗯,很明显。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心脏上那个软糖大小的结节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据我所知,癌症在城里待得越久,就越会破坏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做了任何脱衣舞娘都会做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女孩们。脱衣舞俱乐部的更衣室可以是女性力量的强大核心,也是惊人的信息来源,就像女巫会或缝纫圈一样。脱衣舞娘说肿块很常见。他们还坚持要我去看医生。
在老城诊所,我的执业护士达纳·莫泽(Dana Mozer)彻底抚摸了我。在检查了我乳房的每一厘米后,她说我的肿块不太重要。像我这样的好肿块,可以四处移动;坏的肿块顽固地呆在原地。好的肿块也会增大或缩小,有时取决于咖啡因的摄入量,所以我们又安排了一次约会,我减少了咖啡的摄入量——但两周后,我的肿块还是一样大。尽管我只有33岁,没有癌症、乳腺癌或其他疾病的家族史,她还是为我预约了第一次乳房x光检查。
如果这对你们来说是处女地,乳房x光检查包括把一个人的乳房压扁,就像两块硬塑料盘子之间的煎饼一样,然后拍照。事实证明,煎饼师傅很难抓住我的小乳房,所以不得不重复几次扫描。接下来,我做了超声波检查,它可以发现乳房x光检查没有发现的异常。乳房x光造影师和超声波技师都认为我的乳房看起来完全正常。我松了一口气……直到负责检查的医生进来,拿着我的照片,粗鲁地指出一小把白色的小点——钙化物,怀疑是癌症。她要求进行活组织检查。
我噘起嘴唇,试图掩饰我的愤怒。到目前为止,医生的预约主要是不方便的,但是活检呢?这意味着我失去了一大块乳房!这也意味着我可能有严重的问题,但我能想到的只是这对我的抵押贷款意味着什么。胸部少了一块,我要怎么脱衣?这一块有多大?我能把它藏在德马布伦德那里吗?
等待
《等待》是我最喜欢的伪装者乐队的歌。它的朋克精神引导我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期。但在我做活检和《电话》(伪装者的另一首伟大歌曲)之间的48小时,是一首焦虑不断升级的交响乐。
我努力把这些问题抛诸脑后,并说服自己那些小白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幸运的是,这是我妈妈十年来第一次来看我和哥哥合租的房子,所以我忙着为她的到来做准备,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我对父母只字未提我胸部的奇遇。我想,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我就省了他们的痛苦,在圣诞节(希望如此)我正在康复的时候告诉他们。如果我没得癌症,为什么要让他们担心我得了癌症?
到了周五,我的成绩已经过期了,我正在悄悄地失去它。我给我的执业护士留了言,然后去了我在伦敦东区的调酒班,十个朋友碰巧突发奇想出现向我打招呼(这显然是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迹象)。医生办公室留言时我正忙着端酒。我走出去查看了一下。
在8月下旬的阳光下,温特沃斯雪佛兰大楼非常明亮,棱角分明。这座建筑可能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躲在它的阴影里,向它祈祷,我们的情况不会改变——它会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而我仍然是街对面那个健康的酒保——我的语音信箱里只有好消息。
“你好,万岁。你和外科医生的预约是下周五上午10点。”
我的肚子一沉,双手开始颤抖。去看外科医生的原因只有一个:割掉什么东西。我疯狂地拨通了执业护士的电话,希望能在她周末开始前联系上她。当我接通她的电话时,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伤和同情,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她说,这是导管原位癌零期,她很抱歉。
我回到酒吧,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得了癌症,然后在他们崩溃的时候努力振作起来。我总算熬过了轮班。我开车回家找我哥哥和妈妈——刚从明尼苏达州坐飞机回来——和他们聊天,直到他们上床睡觉。然后我退到我家后门廊,终于哭了起来。

外科医生的女孩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癌症在我身体里扎营了多少,只要用一把刀和油灰,就能轻易地根除,就像补牙一样。事实证明我错了。谢天谢地,判决出来的时候我有我的朋友特瑞娜陪着我。
特瑞娜是一个热情的,永远微笑的红发女孩,她会为朋友做任何事情。2007年,33岁的她在第一次分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诊断出患有2B期乳腺癌,她经历了双侧乳房切除术,化疗,放疗,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变化。她早上请了假开车送我去赴约。
在遗产好撒玛利亚人医院(Legacy Good Samaritan Hospital)的外科医生候诊室里,我翻阅了可用的文献。所有东西都是粉红色的,寄给“幸存者”。
我已经讨厌关于癌症的语言了。这是战争的语言:“战斗”,“战斗”,“幸存者”。说实话,我当时还没准备好。过度工作让我筋疲力尽,心碎了,在抑郁中生活了20年后,我真的厌倦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不想打架呢?如果我不想加入幸存者集团呢?
“你称自己是幸存者吗?”我问崔娜。
“当然,我喜欢!”在化疗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能做的就是熬过这一天,”她说。“我掉了头发,双乳,还有疯狂的伤疤。当然,我是幸存者。”
一个活泼的年轻助手把我们领到一间检查室。她是如此的阳光和可爱,当她告诉我她有我所做的一切原位乳腺管癌零阶段——我已经做了双乳切除手术,但我并没有死于休克。在完成乳房重建后,她显然对结果很满意。“不用再做乳房x光检查了,我不必担心复发,虽然我对自己35岁的乳房并不不满意,但我的新乳房看起来就像20岁一样,”她滔滔不绝地说。“它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很难分享她的热情。
根据我在网上做的研究,我的外科医生娜塔莉·约翰逊(Nathalie Johnson)是西北地区最好的乳房外科医生之一,在每次乳腺癌宴会和活动中都获得了众所周知的金乳房奖。当她走进检查室时,她浑身散发着温暖和力量。她也很漂亮,深棕色的头发在太阳穴处略显灰白,她的皮肤是金棕色的,她的微笑很灿烂。我立刻觉得我可以信任她,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直到她说:“双乳切除术。这是我推荐给35岁以下女性的治疗方法。”
我觉得我的眼睛湿润了。即使听了助理的开场白,我也没想到会听到这个词乳房切除术.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意味着我失去了乳房,而是因为它突然把生育——我一直梦想着,但并不完全在雷达上的事情——置于前沿和中心。
“护理呢?”我无力地问。
“很多女性还没做过乳房切除手术就不能喂奶了,”助手说。“只要说服自己,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并接受这一点。”崔娜和约翰逊大夫都同意了。两人都承认在喂奶时遇到了难以置信的困难。
我们再次在会议室里讨论我的选择。我很幸运有选择——癌症很早就被发现了——但这并没有让做出决定变得更容易。助理给了我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的电话号码,她最近刚做了乳房切除和重建手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她和你一样——单身。”
是的,我是单身。特瑞娜很好,但在我和她的王子丈夫和漂亮的孩子见面后,她就要回家了。我会一个人睡。也许永远都不会,因为两周后,我就要失去双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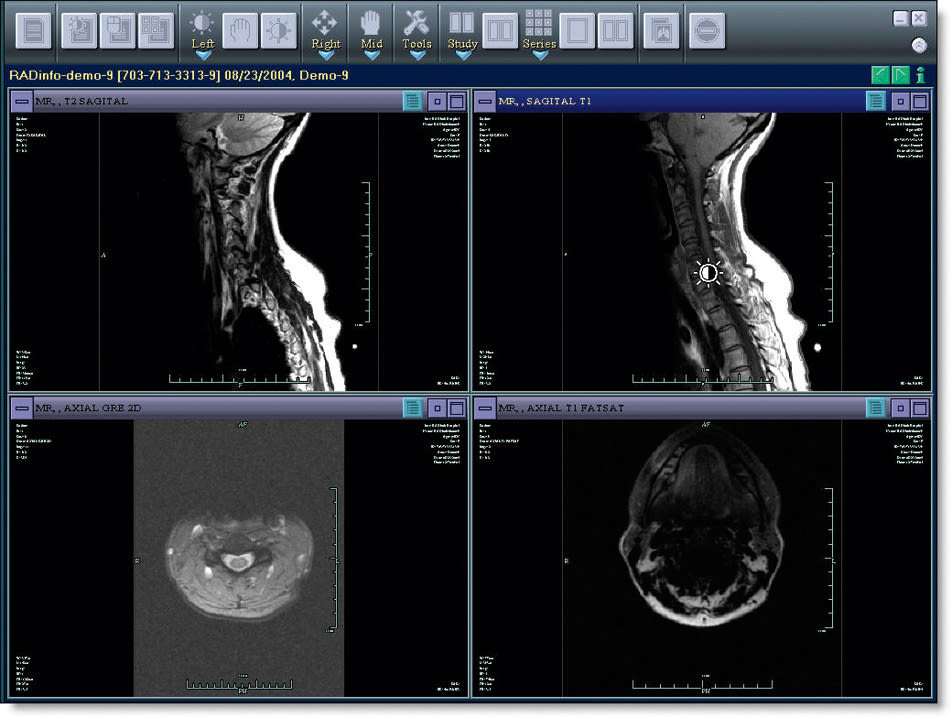
该死的点。我的电影展示了dcis
带来坏消息
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得了癌症。我觉得这是个人的失败,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很软弱,很脆弱。我不想扮演“病人”的角色,也不想让人们对我有任何不同。但现在我不得不请几个月的假,接受一个大手术,是时候坦白了。
为此,我主要依靠短信:“坏消息。得了癌症。两周内切除双乳!令人难以置信的。”
电话打得我应接不暇。我的朋友们非常愤怒,不相信,崩溃了。不是他们安慰我,而是我自己安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诊断的细节和积极治疗计划的原因。每个人都认为双乳切除术是野蛮的。为了替我的医生辩护,我引用了一些统计数据,每一次交谈,我的现实都变得更加真实,我也更加平和地面对它。当我去调酒师当班时,我已经可以对我的新笑话冷嘲热讽地笑了:“你听说我要隆胸了吗?”还有纹身!”
认识我的人都惊呆了。我当了十二年的脱衣舞娘,但除了几个辛苦挣来的伤疤,我的身体从青春期起就没变过。在我的工作中我见过很多很棒的隆胸手术,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隆胸。同上纹身。我在脱衣舞台上的表演都是真诚的,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赤裸的真实的我。更不用说我一直是个假小子,还是个运动员,我喜欢我那几乎露在外面的奶子。我是最不愿意用硅胶胶垫代替她乳房组织的人。
“你? !假的乳房?为什么?”
“嗯,它是免费的!”我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因为……我得了癌症!”
我觉得我的笑话很好笑。不管和我说话的是什么顾客,他都会喝一口威士忌,试图辨别我是否认真。我会喋喋不休地说我的纹身。重建的一部分包括在我原来的乳头上纹身。我想,如果保险公司打算支付纹身的费用,我还不如纹个很酷的纹身,比如雷蒙斯乐队的徽章——上面有一只拿着棒球棒的老鹰——或者把我另一个前男友的名字“白痴”纹在我的胸前。
在酒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调查。人们显然认为我会更沮丧。我不是。得了癌症确实很糟糕,但我没有感到沮丧,甚至没有悲伤或愤怒。事实上,我感觉比以前更踏实了,可能是因为我的焦虑可以集中在一些事情上,而且,这一次,我对近期的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虽然我才刚刚开始接触癌症,但癌症似乎比心碎或抑郁容易得多。即使是被想要杀死我的东西入侵的想法,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并获得了相当大的解脱。
一天晚上,在伦敦东区,我拿出一支笔,画了一张折线图,并给它贴上了“一连串糟糕的事情”的标签。心碎是最糟糕的事情,宠物的死亡也是如此。癌症无疑比飞行或中学更糟糕,也许甚至比朋友的背叛更糟糕。但我真的认为心碎是最糟糕的。或者,也许是战争。不!城市扩张.毫无疑问,城市扩张是我能想到的最具腐蚀性的东西,是悲伤和绝望的持续来源。癌症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它更倾向于那些不那么糟糕的东西。
我最好的三个女朋友——脱衣舞娘、艺术家和学校老师——打断了我的遐想。我的诊断让他们和我一样困惑。他们来到伦敦东区,喝着缓和的鸡尾酒,了解细节。
“你怎么喂奶?!”你知道初乳对宝宝有多重要吗?还有母亲!没有孩子但心地善良的学校老师尖声说。我真想揍她。
“哦,上帝。护理并不是什么大事,”脱衣舞娘说。“但是,Viva,你怎么活下去呢?”你要请多久假?你有保险吗?我们得嫁个有钱人!现在!”
艺术家吸了一口烟,说道:“我不是一直说你会是一个出色的花瓶妻子吗?”
我感觉就像在看自己人生中的希腊悲剧,我的闺蜜们在合唱,说出我最大的三个恐惧:我无法哺育我理论上的孩子。
虽然我有保险,但我没有多余的现金来维持我不得不旷工的三个月的生活。我的脱衣舞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了。
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花瓶妻子。或者本该如此,直到癌症吞噬了我的胸膛天知道我的内脏发生了什么。我想我再也不会约会了。
反抗!和研究。
随着我对诊断的震惊逐渐消失,恐惧和怀疑开始浮现,还有无数的问题。我真的有去做双乳切除手术?我需要做什么吗?如果我做了手术,我怎么支付我的账单?我的摇滚乐队还能在万圣节演出吗?
还有,为什么我在33岁的时候得了癌症?这根本说不通。我总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跑步、游泳、定期针灸,近二十年来一直是素食主义者。是的,我在烟雾缭绕的酒吧工作,但每周只有10到15个小时。我从不吸烟。我喝酒,但很少过量。罪魁祸首一定是压力。还是……
朋友们插话说了各种没用的数据。例如,上夜班的女性显然比上白班的女性更容易患乳腺癌。另一个你不会在广告上看到的数据是:生活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在美国是最高的,一些专家将其归因于缺乏阳光。一位朋友把我的癌症归咎于我在一次不明智的日光浴床经历后遭受的严重晒伤。另一个朋友责怪我的前任:“癌症就在你的心脏上。你可怜的心脏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这肯定是有关系的。”
我的下一步就是反抗。这些医生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密谋对付我?我的癌症是阶段零.在我的书里,零意味着“一无所有”。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呢?我想得越多,就越喜欢这个选择。我可以保留我的乳房,密切关注其中的流氓细胞,并开始定期冥想。有些人称之为“否认”;然而,我决定我需要另一个意见。
很快,我就有了一份广泛的自然理疗师、针灸师和乳腺癌“幸存者”的名单来咨询。我花了几个小时上网收集信息。我的电话费已经用完了。我阅读了所有的乳腺癌圣经,喝了抗癌药水(小苏打和枫糖浆,谁喝过?),研究了榨汁机(以开始推荐的生食饮食),报名参加了乳腺癌瑜伽、针灸,甚至还有一个癌症写作小组。我尽可能地和每一位乳腺癌幸存者交谈,和他们一起喝酒,在时髦酒吧的黑暗浴室里摸他们重建的乳房。我把我的病理报告传真给全国各地的医生朋友们。毫无例外,每一个治疗师——无论是嬉皮士、整体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还是正统派——都坚持要我用手术切除癌变组织。立即。
然而,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我慌了。我取消了手术,并安排了约翰逊医生的另一次会诊。
为了精神上的支持,我拉着弟弟一起去。我们发现约翰逊医生穿着外科手术服,大概是为一天的乳房切除做准备,其中两个应该是我的。她平静地回答我的每一个怀疑、恐惧和问题,包括我什么都不做的幻想。但她对我的态度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严厉多了。我们检查了我的乳房x光片。我第一次看到它时,那些白点看起来是那么无害;现在,在癌症新兵训练营呆了两个星期后,他们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的更邪恶,数量也更多。据约翰逊医生说,我需要他们离开那里,尽快.我强忍着眼泪,心里明白她是对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给父亲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写这封信简直要了我的命——这个消息会伤透我父亲的心。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们是一个健康狂人和运动员的家庭。没有人患癌症。除了我没有人。
谢天谢地,那天下午我在玛丽家值班。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最想和我的舞蹈家在一起。他们慷慨大方,善解人意。他们知道依靠身体谋生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身体让你失望时隐含的恐惧。
一年一度的科曼波特兰治愈赛就要开始了。玛丽俱乐部更衣室里的一张巨大的报名表上写满了名字——女孩们将与她们死于乳腺癌的所有人的名字一起行走。
比赛那天早上,我们一群人聚集在玛丽家外面。是早上八点非常早期的脱衣舞女。但我们就在那儿,裹得严严实实抵御着寒冷的秋雨。我们一起漫步到海滨。预计将有4万人参加,当我穿过气球、帽子、头巾和假发时,我很快就不知所措了。
我看见三个穿着卡哈特工作夹克和靴子的牛仔——高大、强壮、英俊,因悲伤而弯着腰。他们举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张照片——我想是年长绅士的妻子和年轻绅士的母亲。我一看到他们就说不出话来。
五天之内,我的乳房就开始萎缩了。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治愈疗法竞赛。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对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低声说。“我们还是喝点解药吧。”
我们和人群一起沿着百老汇西南大街游行,经过玛丽俱乐部,然后拐进了烬酒吧的前门。一位出色的酒保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为我们倒上了浓郁的爱尔兰咖啡,并在粉红色的队伍庄严地驶过时提出了尖刻的时尚评论。威士忌咖啡喝到一半,我感觉好多了。我们同意让“为治愈而饮”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
接下来的四天是一片混乱。我和我的出版商见了面,我的书将于8月出版。我的乐队可可眼镜蛇和杀手又排练了一次,希望我能回来参加我们在东区的万圣节表演。我坐下来拍了一组照片,和我最爱的写作小组一起,在我的前院种了数百棵春天的鳞茎。显然,手术后生活还会继续。我只是不太确定它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整形外科医生布鲁斯·韦伯(Bruce Webber)和我讨论了许多人一直以来的建议:只取癌变的乳房,而别管另一侧。
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有更认真地考虑这个选择是很奇怪的。我被信息淹没了,考虑了十几个不同医生的意见,我认为我的选择要么全部(双乳切除术),要么什么都不做。感谢上帝有韦伯医生。我喜欢他跟我说话的方式:没有废话,一点也不居高临下。我信任他。在他的建议和赞同下,我做出了决定。随之而来的轻松令人陶醉。我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混乱、悲伤和恐惧。我会失去乳房,但我会保持理智。

韦伯医生:他真是个艺术家。
世纪派对
于是,在9月26日,我接受了单侧乳房切除术。约翰逊医生切除了我的左乳房和几个淋巴结进行活检;韦伯医生给我植入了一个组织扩张器,开始了重建过程,然后给它注入了生理盐水,把我缝合了起来。
由于我左乳钙化的程度,有人担心我的癌症可能是侵袭性的。手术后,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淋巴结干净了。医生还告诉我,我的乳头已经被抢救出来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可能的。我又睡着了,如释重负。下次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派对上了。
我妈妈和我纽约的朋友都飞过来了。学校老师请了一天假,我哥哥站在旁边听我的吩咐,给任何关心他的人发短信更新。
很多人都很关心。他们聚集在我的病房里,喝着酒,看总统辩论,在我从麻醉中苏醒时陪伴着我。到了第二天下午,派对已经超出了我的病房,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换换环境了。护士一解开我的静脉注射器,我就出了门。学校老师开着她61年的淡蓝色保时捷来接我,我们时髦地骑到我家。
在我短暂的休假期间,有人彻底搜查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鲜花,我的狗已经被租出去了(我接到严格的命令,两周内不能走路——甚至不能绕着街区走一圈)。客人们几乎马上就来了,带着更多的鲜花、杂货、书籍和dvd。我妈妈准备了一大锅鸡汤,而我的替身妈妈,玛丽俱乐部的老板薇姬·凯勒(Vicki Keller)则在评论菜谱。一瓶又一瓶的酒被打开喝完了(不是我喝的),而我像埃及艳后一样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沐浴在所有的爱和关注中。
该党稳定地维持了两个星期。我甚至不认识的人带着砂锅菜和炖菜出现了,而久别重逢的熟人又出现了,他们讲着故事,生着孩子,为我的恢复期增光添彩。我从不向任何人推荐癌症,但我不得不说,手术后的几周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之一。
每天都有小小的胜利。尽管我听到的大多数乳房切除术后的故事都是病人躺了一个星期,连睡裤都不能整理,但我坚持不穿休闲服。当我找到一件可以套在我那大片绷带上的裙子时,我欣喜若狂(一个女性朋友说我看起来像穿了Azzedine Alaïa的衣服),当我发现我可以用一只手臂小心地穿上牛仔裤,然后扣上拉链时,我欣喜若狂。洗头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像我第一次洗澡一样。特瑞娜过来帮我做后一件,我们一起打开了我新的身体部位。
我不敢看。但当崔娜喘着气说它看起来很棒时,我偷看了一下。确实有一个乳房。一个青一块紫一块的、结痂的、肿胀的乳房,但毕竟是乳房。

沙漠修道院的基督
图片:拉斯维加斯万岁
摩托车、僧侣和金钱
这本该是故事的结局。我的乳房切除术本应“治愈”我。我打算,几个月后,再也不去想乳腺癌的事。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对我乳房组织的解剖发现了一个极具侵袭性的小肿瘤,这增加了淋巴血管侵入的可能性。通俗地说:虽然我的淋巴结很干净,但癌细胞可能会有从乳腺导管逃逸进入血液,它们可以在我身体的任何地方传播,最不祥的是到达我的骨骼,肺或肝脏。
“可能”这两个字使我相当惊愕。第一次,我被分配了一个肿瘤学家,然后是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统计数据对我有利:手术“治愈”我的可能性有80%到90%,但如果癌症扩散并侵入我的骨骼、肺或肝脏,几乎可以肯定是致命的。虽然化疗只把我本来就很渺茫的复发几率降低了30%,但三分之二的肿瘤学家还是推荐化疗,每个自然疗法师、针灸师和朋友都这么建议。
我又一次面临着一个痛苦的决定——让我的身体接受化疗,是否值得这样轻微的风险降低。我的处境又一次让我感到困惑。我很幸运:我有选择。许多女性在发现自己患有癌症时,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可以选择是否要化疗。不过,对我来说,做决定是最难的部分;做决定并不是什么奢侈的事。
在考虑了四个星期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收集专业意见后,我彻底崩溃了。如果说我以前不想为自己的生命而战,那么现在我更不想了。通常当我这么低的时候,爬到摩托车后面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尽管整形外科医生在术后两个月内禁止这样的活动,但我觉得利大于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骑着一辆旧本田在西山兜风,用我那只完好的胳膊紧紧地牵着一匹田纳西种马。在那宝贵的几个小时里,我感觉又像回了自己,这种积极的影响持续了整整两天。
协议要求我在手术后三个月内开始一个疗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沮丧。我无缘无故地哭了起来,我的心几乎要崩溃了。当我的疾病威胁着我的未来时,钱的问题变得更加令人苦恼。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工作,也不知道该怎么付账单。如果没有我的朋友,我可能已经迷路了。他们为我提供食物,招待我,每次我只剩最后六块钱的时候,就会有英雄带着一箱汽油,一袋食品杂货,一次免费按摩,一堆几百元的钞票突然出现。
最后,也许是听到了我声音里的痛苦,我心中最大的英雄开始了他的营救计划。多年来,身为路德教牧师的父亲一直鼓励我去修道院,并向我保证,那里的沉默和祈祷会让我集中精神,扎根内心。父亲深信我在沉默中需要阳光,坚持让我去南方旅行,并为我预订了在查马峡谷沙漠中的基督修道院的住宿,就在新墨西哥州Abiquiú小镇的北部。
这就是我去年11月与20位本笃会修道士共进晚餐的原因。我祈祷,冥想,吟诵,在沙漠中徒步旅行。慢慢地,我回过神来。几天后,我的眼泪就干了,我觉得我的灵魂开始回到它的中心。待到最后,我的假笑又回来了。在一顿沉默的午餐中,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无数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在一屋子男人里——但在过去,我几乎总是裸体。
我从新墨西哥州快乐而平静地回到家,我见到了我的肿瘤医生布鲁斯·戴纳医生,头脑清醒,心胸开阔。我意识到,与我所谓的缺乏斗志相反,我从确诊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战斗。我在与损失抗争,与变化抗争,与现实抗争。尽管我最终承认了生活值得为之奋斗,也许奋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一旦我放松下来,我就做出了决定:我要做化疗。
性、毒品和摇滚

可可眼镜蛇和杀手
图片:拉斯维加斯万岁
治愈是一个过程,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我的身体和思想不得不以癌症前我认为不可能的方式伸展和成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有信心,到夏天我就能穿上一个可爱的新架子。我很期待化疗后的朋克发型。希望我的思想能像时尚一样反弹(如果不行,新墨西哥州总是有那些僧侣)。
我的左乳已经伸展到可以承受两次巨大的生理盐水注射。对我来说,它看起来很大,尤其是在我的a罩杯右胸旁边,但这并不妨碍我在万圣节Coco Cobra和the Killers的演出上穿着渔网衬衫炫耀它们。化疗结束后,我的两个乳房都将接受另一次手术:左乳的扩张袋将被硅胶植入物替换,而我的右乳将被扩大到与之匹配的程度。虽然这不是我曾经渴望的,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一个合适的海报身材。
我会认真地研究一段时间的药品。化疗结束后,我将开始为期五年的他莫西芬治疗,并每周注射一年的赫赛汀(Herceptin)。赫赛汀是一种设计药物,每次注射价格在8000美元至1万美元之间,将使我成为“金手臂女孩”。我更愿意计划在纽约休假或者怀孕,但现在,这些事情都被搁置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会待在波特兰,享受朋友们的爱,玩音乐,宣传我的书,同时安慰那些刚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女孩,让她们在时髦酒吧的黑暗角落里感受到我的存在。
也许,只是也许,我会在我非常喜欢的市中心脱衣舞夜总会的舞台上客串几次,在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伴奏下,赤身裸体地闲逛,宣扬所有的身体,无论经历过什么奇怪的冒险,都是美丽的。





